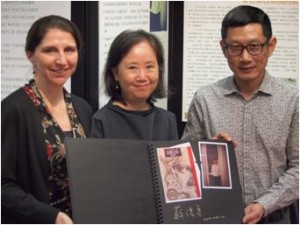访问:汪来昇、陈文慧
撰写:汪来昇
访问稿整理:房振坤
摄影:郑伊婷
校对:邱勇康
“我的写作一直就是陌生化的过程。我也希望一直保持这样的陌生化的写作状态,看待这个深深眷恋的人世。” —— 苏伟贞
于2013年8月16日,南大中文系为国际驻校作家,苏伟贞老师在中文图书馆的作品展,举行了开幕茶会。起初接获崔峰老师邀请撰写报导时,因毕业论文的压力迫使我有种想回绝的意思,但我却莫名地,还是接下了这份重要的“任务”。我想,与其平面地报导当日盛况,不如让这份“任务”增值,变成一份更有意义的记录。于是,我选择了以访问的形式,与苏老师有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意外的邀请
苏老师收到南大的邀请时,她正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起初,她并没预期至南大中文系驻校,加上满载的行程似乎也难以调配。然而游俊豪老师展现的诚意及空间,加上练习着与新加坡的旧日因缘,终于,她到了南大。这就是现在我们可坐在这里访问她的理由。
第三次到新加坡
以往在新加坡,是公事邀请,因此来去都有人接送,失去了近身体验新加坡生活、交通的机会;可是这次,苏老师选择到朋友家住,拉近了她与地方的距离感。苏老师不再被动地,从一个区块移动到另一个区块,而是真实地感受远、近空间感。
对她而言,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小市民生活的乐趣。就算只是在组屋区楼下的咖啡店里,喝啤酒吃小菜,都是令她羡慕不已的事。她与咖啡店服务生的交谈,也加深了她对新加坡民生和语言的认识,例如“放工”其实指下班。
课程亮点
“原来课程就是两个字:写作。我的心里就窃窃欢喜。”
原先,苏老师设计课程时,是针对一个比较多元的,以五四以降的现当代文学(中港台和东南亚),形成一条轴线来带领同学们进入文学世界。后来,她获知课程项目是“写作”,事情好像较有重心;她还调皮地说:“我心里窃窃欢喜。”
可是在她的课堂中,初步接触,她其实大量给同学们介绍一些作品及理论,希望从中能唤醒大家内心,受文学触动。她甚至有计画的在台湾编好一本三百多页的教材文本,从台湾寄来,送给学生,也方便讲授。
“你们人生还有很长的路程,这一段时间,也许会变成你们在文学上,可能甚至是唯一,最短暂却最深刻的接触。”
她希望自己离开南大后,她举例,同学们看到月亮时, “不再只是看到一个月亮”,而是能过一种看的方式,透过 “文学的心”,以较丰富的文字意象传达出来。她希望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打动同学内心的撞击者。
写作的初衷
每个人,每天都处于变化中,更何况是为作家。苏老师自第一本小说集《陪他一段》享誉了华文文坛32年,她是否能保持着那份初衷?
“其实这些年来,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一种陌生化的感觉…… 人人都活在一个日常生活里头,对习以为常的事情会变得冷漠枯燥,不会去感受。我觉得我自以前我是一个“意见者”,发誓永远要对这个世界有意见…… (不去感受的日常生活)容易使人庸俗。”
我想,“初衷”对于许多作家而言,书写时并不那么意识;但唯一确定的是,像苏老师这样的作家,她无法只是平凡。对她来说,很多事情都愿意通过“感知”去了解,而不愿意追本溯源地挖掘真相。如果说,老师的书写一直保持着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她的“感知”便是一种独特的个人“感受”。正如2005年范铭如与老师做过的访问中(《印刻文学生活志》第24期,2005年8月号),她认为“感觉”是无法与任何人“感同身受”的。
我继续追问:是否因此,您的文笔才极为细腻的去刻画人物的心灵感受?
“我并不认为我比别人感受得深刻,可是就是‘不一样’。就像同一个时间在地球上诞生的人,他们的命运不会是一样…… 我并不是说别人不了解我,就表示我比别人深刻。我写细腻是因为我本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人。我不写细腻,我没办法往下写。但比较难的是,我要怎样展现出来,我跟别人感受不一样的部分。 ”
不肯沉默的心
我在准备苏老师的访问时,翻阅了许多台湾文史与评论,几乎每一篇都指向《沉默之岛》为她的经典之作。我在网上搜索时,发现《沉默之岛》竟然是绝版书,本以为必须要到图书馆借才能阅读得这本经典。可是,机缘巧合下却在(上学期)第一届本地驻校作家,英培安老师的草根书室中寻获,像是挖到宝一样。于是,我开始很认真地阅读这本小说。
作为一本开创新时代观点/性别/情慾/跨越空间/身世议题的小说,起初读起来不容易,像是在苏老师许多形而上的思绪中游移,如果稍不认真,就会迷失在茫然的大海中,而超高密度的文字,不断地阻碍着我的前进;所以为了完成阅读,我必须顺着作者思考的巨浪 —— 这才令我找到了陆地。
苏老师认为《离开同方》是她对眷村生活的小告别,而《沉默之岛》则是向情慾书写告别,象征了一个书写的“新开始”。
“《沉默之岛》形同打开了一个视野,意思说,你好像可以飞高一点,看得清楚一点了。”
苏老师的《沉默之岛》享誉中外,(甚至即将在新加坡翻译成英语出版),被南大中文系游俊豪老师评价为“世界级的小说”。许多学者在分析这一篇小说时,就断定了作者是位“女性主义作家”,包括陈芳明的《新台湾文学史》也将苏伟贞放置于“80年代女性小说崛起”时段里。
汪来昇:不同学者给予您不同的评价与地位(眷村、女性主义等),我好奇的是您怎么定位自己?
苏伟贞:眷村小说这个部分,其实是我的一个身份。我出身眷村,眷村书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族群的创作。我很高兴自己是其中一员,我很喜欢眷村小说这个名称,我也希望自己在眷村书写这件事上出过力。我愿意在这个身份被贴标签。至于女性主义作家,会不会有点“开倒车”?伍尔芙(Virginia Woolf)作为女性小说的先驱,为女性发声,告诉世人,一个女人要自己的房间,呼吁思考。(女性主义)究竟是个限制呢还是个贬义词呢或赞美呢?
汪来昇:那您当时写《沉默之岛》时,有意图刻意把女性主义、权利的东西放进去吗?
苏伟贞:完全没有。《沉默之岛》可以说是个情慾“无性生殖”繁殖的实验,正是要去女性主义化。它同时是个雌雄同体的概念,她(晨勉)可以得到一个自身的满足。我要说的不是情慾上的满足,而是一种试探,人类的身体可以大到深化到什么程度。
汪来昇:《沉默之岛》中,有种令人穿梭时空的感觉。小说情节和晨勉思绪的广度和深度惊人;这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是否有紧密的关系呢?
苏伟贞:完全没有。但我觉得这和我长时间坐在那边(案前)有关系。我不知道别人的生活,可是我感觉和猜想,大部分人的一生也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我觉得我的生活都是我能够承受得住的。那剩下,可能只是一个对远方的向往的状态。所以在《沉默之岛》里头那么大跨度的,可能是对不安定的一种渴望。我们的生活都太密集了,包括生活的空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想要抽离,不断地在旅途上抽离。可是我是一个糟糕的旅行者,我去到哪边,我就在上面不动的。可是“另一个我”就时常代替我不断的抽离到别一个地方去。创造出来这样子的人,代替我狠狠的过另外一种生活。
如果说《陪他一段》开启了苏老师这颗敏锐的心,《沉默之岛》便是召唤她内心最深刻的自我,在沉默之中透视周遭和自省的著作,与文字零距离最亲密地接触。虽然时空无法束缚一位作家作品世界里的精彩、跳跃与开阔,但是到头来伏在案前书写的仍然只剩下自己。我想,切实面对被召唤的内心,才能在文字里展现出一种“孤独却坚持” 的张力。
曾经沧海
在整理访问问题时,我刻意标上“这题可不作答”,害怕苏老师觉得我过问她的“私事”。不过访问时,她虽然眼眶泛红,却还是和乐观勇敢地与我们倾心。我想,我不应该在这一题上“整理”苏老师说过的话,而是让一位作家真情流露地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汪来昇:您的两部作品《时光队伍》与《租书店的女儿》,得知是您失去了生命中两位最重要的男人后写下的。在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对您的写作或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苏伟贞:这样说吧,我先生跟我爸爸都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原型,我其实现在还不是那么能谈这件事情。而且,我先生可以说是我最好的一位读者,他的位置一向很抽离。我们会亲近,就是因为他看了我的小说,他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写作要求十分严格。我想我知道他的想法: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
有时候论者会把“张(爱玲)派”作为一种流派,纳入某些作家,他(丈夫)会澹澹的说:“其实你的视野已经比张爱玲宽了。”这当然是一种鼓励,以他的形式。所以他离开,然后要写他,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有这样的可能。因此,当我决定写他的时候,也看了一些人追悼文章。我希望可以告诉他(丈夫),我写得不比他们坏(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以夫之名吧。把他的一切有形无形都写到底,所以,我跟小孩说,你们不太了解自己的家谱,因为先辈是从大陆去的台湾;我还同时跟孙子讲,你们以后要是不知道张家排行辈分,就去看《时光队伍》。孙子不记得他爷爷的样子了,他(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才一岁左右。但是我说,这本书,在这里头,你会知道你爷爷是怎么样子。主要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先生的后人写的。
可是我真实世界已经找不到、可以那麽自觉的保持自己一贯人格的他了。我不知道该把他放在一个怎么样的容器里头来写。藉由我先生生病表现在状态,我觉得说,他和一些我响往的人格者真的是一支队伍裡的人,他们朝向一个我们开不见,但是仍然在行走进进的时光隧道隐去。
所以写完后,一直到现在,我陷入一种深深不太想写作了的情况裡,我居然用先生来当题材来写作。这真的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但想想,我一直想要告诉他,他走以后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又开始慢慢写了,他走以后,我们一起曾经去过的地方,现在变得什么样子了,作为一个报信者,我要告诉他。
至于我的爸爸,他的过世,其实代表我们家在台湾岛上面的一个开始与结束。我父亲1949年跟着部队从广东到了台湾,等于说连根拔起。我们在台湾除了姑妈没有其他亲人。我爸跟姑妈很亲。我这一代,是“伟”字辈,也是父亲所知道的我们广东老家谱系的最后排行。
我父亲到了台湾以后,有了第三代,于是就自己拟定了一个新族谱“立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转化自文天祥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但我父亲以“立”代“养”,这跟他出身军旅有关。我的父亲的过世,等于属于苏家在岛上的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排序延续生命,即使我父亲不在了。
当然,年纪大了,回头看父亲他们一代,以一个移民的身分被抛掷到台湾,没有任何资源,辛苦拉拔小孩长大。举目无亲,以现在的眼光看,我都会害怕,但是他们没得怕的,(只能)向前走。
我爸做过很多事情谋生,一个腰杆挺直堂堂正正的男人,他从不抱怨,自己承担。人家(父亲)以前也是个公子哥儿,在家里大爷似的,所以这样的结束一生,我认为对我父亲来说,不是一个坏的结束,他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我会一直牢牢记得回台南成功大学教书是为了我爸爸的那份初衷来做为我这一生行事的准绳。因为我知道他从来都没有料到,他有一个女儿,可以到学校当教授,而且是台南这么好的学校。那像我当初写作、得奖把他吓了一大跳同样状况。
教书这件事的可能性,在我进军校基本上已经毁了一大半,因为那不是发展学术的地方。但一切时机凑合得如此好,我唸了博士,我从原本工作的联合报离职,我进了学校教书。我开始积极回台南,是意识到我爸爸没有多少时间。也真的,我回去半年他就走了。我永远都看见,当我重新再做一个女儿,家人们围桌吃饭的时候,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坐在旁边,脸趴着桌面,一直望着我们一直微笑。他严重的重听,视力也很坏,看不见听不见,体力也差。子女们几乎都回来了,在他人生最晚的晚年陪伴着他。那个无声的画面,想着都心痛。
所以父亲过世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他走后,之前之后纪念他陆续写成了《租书店女儿》,那样的纪实有所本,对我只能以散文的形式来写。
是啊!父亲对我的影响永远大过其他作家。
给南大中文系学生的一句话
“写作永远不会太迟,因为人一直活着,就是一直在为写作这件事做好准备。”—— 苏伟贞
稿于:2013年8月25日
文章来源:华文文学创作暨驻校作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