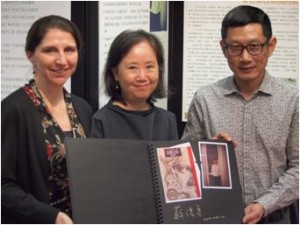精彩活动 Events
“租书店的女儿”——苏伟贞

“人世当中,作家所写的,其实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个‘谁’在里头,都有父亲,都有情人,或者也都有仇人。对我而言,《租书店的女儿》是一个形式的悼亡之书,为了一个时代,为了一些人,为了一段记忆。”
对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国际驻校作家苏伟贞教授来说,记忆的书写是其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特色,亦是作家的创作来源;而在她最新一本散文集《租书店的女儿》当中,其主要追忆与缅怀的对象便是父亲——苏刚。
其父亲苏刚在苏伟贞人生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她过去的日常生活,还是在她的内心深处,父亲的位置举足轻重亦无可动摇。在苏伟贞的笔触之下,父亲的一生有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巨型画作,絮絮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苏刚对于苏伟贞而言除了是父亲,也是其创作的源头。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父亲,才有了“租书店的女儿”;因为父亲,才有了现今台湾著名“鬼才”女作家——苏伟贞。
其父亲苏刚在苏伟贞人生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她过去的日常生活,还是在她的内心深处,父亲的位置举足轻重亦无可动摇。在苏伟贞的笔触之下,父亲的一生有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巨型画作,絮絮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苏刚对于苏伟贞而言除了是父亲,也是其创作的源头。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父亲,才有了“租书店的女儿”;因为父亲,才有了现今台湾著名“鬼才”女作家——苏伟贞。
日前,南大中文系与中文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从《陪他一段》到《租书店的女儿》”的讲座,诚邀苏伟贞现身说法,层层剖析其创作机缘。该讲座反应热烈,与会者除系里师生以外,还包括本地著名作家刘培芳与孙爱玲等人。
谈及苏伟贞的创作背景,就不得不把焦点放在苏伟贞父亲生前所开的一间“租书店”。其父亲本是个军人,后因个人事故,中途转行,开了家“日日新租书店”。“日日新”,取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苏伟贞在讲座上这么描述父亲:“穷苦根本不是一件事情。想想看我的父亲,在那个年代里头,从军中退了下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我现在想起来都好心痛。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没有任何亲人,父亲自己建立起一个家庭。从他的工作岗位(军队)上,因为某些事情退下来,没去做别的,一个从黄埔军校出生的男人,却选择开租书店。”
她进一步指出:“我一辈子也不理解我爸爸的想法,也从没听他说过。他只有在我得奖的时候,淡淡地说过‘没想到我开了一家租书店,就能有这样子的成就’。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在为我父亲而写。”
中华民国最小的童工
苏伟贞自小在租书店长大。那一段过去对她而言是甜蜜的童年回忆。 “(我)小学时就帮爸爸看书店,就这样,我每天放了学,人家都去别的地方玩,而我都回家,就在书店看书。”对于当时还是个小朋友的苏伟贞,回想起那一段往事时,她幽默地形容自己为“小童工”。
有时父亲出门了,苏伟贞便得充当起“看店候补”,帮忙经营生意。她笑言:“当时小学一年级,我认识的字不多,爸爸就叫我用画画的方式,把租出的书名记下,就照着那些方块字画。我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最小的童工了。”
因为童年的“打工”记忆,苏伟贞便和各类小说,尤其是武侠与言情小说结下了“情缘”。她在《租书店的女儿》当中这么写道:“刚进小学的我仅能装模作样翻弄落到当包书纸的零散漫画……我白天黑夜天酱在言情小说美女俊男情史里……扫完严沁《烟水寒》、《桑园》,快攻依达《断弦曲》、《舞衣》、《蒙妮坦日记》,或急吼吼追玄小佛《沙滩上的月亮》、《又是起风时》进度,要不来本金杏枝《一树梨花压海棠》、禹其民《篮球情人梦》……”
年幼的苏伟贞就在耳濡目染的成长过程中成了忠实的“小说迷”。每当她从学校里回到租书店,首先便会向父亲询问“依达来了没有?”,接着忙着四处探寻店里是否来了依达等作家的新书。然而,父亲对于这样的“小说控”女儿,总会说一句“谁都没来,人在香港忙着呢!”
至于武侠小说,父亲总觉得女孩子家不宜接触太多“打打杀杀”,“刀光剑影”,于是都不允许苏伟贞接触。因此,她也只能瞒着父亲偷偷地,暗地里与武侠江湖为伴。
后来,苏伟贞考进了台南德光女中,在校内图书馆认识到了张爱玲、白先勇与郭良蕙等作家的著作。从《怨女》到《寂寞的十七岁》和《蝉》,她突然懂得了通俗小说与纯文学之间的差别,明白到“小说除了言情总还有些别的”。
高中时期,苏伟贞更是通过小说《变形虹》,知道了台湾著名作家与编舞家林怀民。在一次林怀民的讲演上,她看到后者缓缓开始以文学的语言叙述自己的舞蹈生涯,接着便当众示范舞蹈动作。这种小说与艺术结合的形式,令人震惊,也撼动了苏伟贞。那是她第一次以读者的身份和作家近距离接触,忽然,她心里涌现一股微弱之声:“如果,我也能写小说呢?”
于是,1979年年底,苏伟贞的处女作《陪他一段》出炉了。对此,她幽默地告诉在场的与会者:“跟别的作家一样,开始写作时,是写自己的故事。可能是失恋什么的,大家自己想。”
《陪他一段》的刊登,是充满着无数喜悦的。忆起这件事时,苏伟贞表示:“《陪》发表在《联合报》的短篇小说。要在当时台湾最大的报纸发表小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是一个对世俗事情非常低能的人。我写完了,就把小说寄出去,然后就等着成为作家。当然,(我)也很幸运就成为了作家。”
父亲——苏伟贞写作的动力
这一路走来,苏伟贞还著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集。《租书店的女儿》出版于2008年,为作者在“父后纪元”所写,记载了她在台南成长的过程与经历。其中,该集的第一篇文章便谈到了父亲晚年的生活。
2006年,苏伟贞回到了台南,进入国立成功大学教书,主要是因为心里有个预感父亲在世的日子不长了。
她说:“我爸爸晚年消磨的方式很不一样,他看武侠小说,一直看,重复着看。于是,我也找到了一个焦点,把焦点埋在武侠里。我告诉自己,父亲晚年不寂寞,因为他看书。我一直以为可以这样子下去。可是,有一天,忽然接到妈妈的电话,糟糕爸爸眼睛看不到了。我立刻从台北回到台南,帮他找眼科医生。爸爸是炮兵出生,所以耳朵在很早时,几乎听不见,现在连看也看不见了。”
有一天,苏伟贞回到家中,父亲突然想要看报纸。惊讶的是,视力已大不如从前的父亲竟然能够念着报纸上的字眼,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把报纸放下。父亲到了晚年仍然坚持着要看书的毅力,启发了苏伟贞创作的决心。
她表示:“这个女儿,从父亲那里,继续展开她的书写,因为她知道她的父亲,一直到他过世之前,都还在读书,都还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期待,期待着租书店的女儿继续写下去。”

文字、摄影:林科宏(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生)
文章来源:华文文学创作暨驻校作家计划
苏伟贞专题讲座:从“陪他一段”到“租书店的女儿” (视频)
从“陪他一段”到“租书店的女儿” 讲稿
从“陪他一段”到“租书店的女儿” 讲稿
苏伟贞
一,写作何以困难?自我建构。
写作永远是困难的,谈写作就更难了。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马奎斯《我不是来演讲的》这篇演讲稿帮助我开场,他开宗明义说,“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 但谈到写作,那种“被逼”,往往可能正是维吉尼亚‧吴尔芙的不能不书写的宿命,“我感觉到在握笔的指端,每个字的重量。”
马奎斯演讲之初,说,“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
和马奎斯一样,我也想毁灭自己,可最后,我还是来演讲了。我的命和马奎斯当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我本来也没想过要当作家。只想当一个读者也就够了。这跟我的背景有关,稍后我们再说。这里要先问的是,所以,什么是作家呢?如何成为专业作家呢?
什么是作家?
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班雅明定义为“说故事的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作家罗兰‧巴特:“作家是一篇作品的创造者。当他说话的时候,意义就开始无止尽的衍生。”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一面探寻,一面揭开存在不为人知的面向。”美国南方文学重镇福克纳的一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致答辞中告诉我们:“人的不朽,不来自他是万物中唯一有着永不停息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能能同情、能牺牲、能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书写这个,诗人和作家的恩宠,在于提升人的心灵,在于重新唤醒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悲悯和牺牲人类昔日一度拥有的荣光,以帮助人成为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为人类留下记录,而是做为人类永存并且真正胜利的真正倚仗和柱石。”也是鲁迅“苦于不能全忘却”的启悟。
有作家的作家之称的阿根廷作家波赫士:“我写故事是因为我相信这些事情,不只是相不相信历史的真伪而已,而是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
波赫士:经典,书本并不真的重要到需要我们去精挑细选,然后要我们迷迷糊糊的崇拜。 (这像宗教了)他爱书成痴,走进书店看见一本极爱的诗集,他就对自己说:“真可惜,我不能买这本书,因为家里早就有一本了。”
那么,做为一名作家,关于“我如何写作”及作息表:
●俄国作家纳博可夫。写有《罗丽塔》。
我冬天时七点左右醒来,我的闹钟是个阿尔卑斯红嘴山鸦,它每天到我的阳台上发出最美妙的笑声。我趟在床上整理规画一下思绪。八点左右;刮脸,吃早餐,进入正式思考,洗澡──就这么个顺序。然后在书房里工作到午饭时,抽空跟妻子沿湖边散一会儿步。 …我们下午一点左右吃午饭,一点半我回到书桌前,工作到六点半。然后漫步在报摊找英文报纸,七点吃晚饭。晚饭后不工作,九点左右上床。我晚上读书看报到十一点半,随后与失眠纠缠到凌晨一点左右。 “描述这份工作日志的当时,一九六四年,纳博可夫,六十五岁。仍宛如老工匠工作方式。
●罗兰‧巴特,着有《恋人絮语》:
作息渡假时,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泡一些茶,切一些面屑给花园里的鸟儿吃,我盥洗,擦书桌…听七点半新闻。八点,母亲起床,我们一起吃两颗水煮蛋,八点一刻,去村里买一份早报,然后开始工作。九点半邮差送信来,十点半我准时煮一壸咖啡,一点吃午餐,一点半到二点午睡,起床后开始游荡,这时我不想工作,有时画画,四点又继续工作,五点一刻,午茶时间,直到七点停下工作,去花园浇花,弹一会钢琴,晚饭后看电视,十点上床,读两本书,很有文学性的随笔或侦探小说或英文小说。
他说:“以上这些,你指出了自己的阶级,你建构自己是作家,……你正在自我建构。”
●莫言写《生死疲劳》四十五万字初稿用了43天时间,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偶尔出去散步。自言:“写小说是个手工活儿”,《檀香刑》是半手工半电脑,《四十一炮》完全是用电脑写的。后来感觉用电脑不舒服,就恢复了纸和笔的写作,非常快,用电脑写时最多一天写三四千字,用笔写,每天就一万多字。原创时用笔感觉真是其乐无穷,如同一个人在真正的林海雪原滑雪跟在室内滑雪场完全不同,每天看稿纸在增高加厚,是实实在在的感觉,用电脑就会疑惑:我写了吗?
●义大利小说家安伯托‧艾可。着有百科全书式学识式的《昨日之岛》:我没有特的方法和固定写作的时段、日子或者季节,但我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身在何处,我随时整理想法、写笔记,打草稿。
●马奎斯呢?他说:《百年孤独》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我从二十岁开始出书,三十八岁已经出了四本。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我只知道,十八个月里,我天天写,没有一天不写,直到写完。
过程中,打字员在一个瓢泼大雨,她带着我修改完毕的终稿回家,下公车时滑了一跤,稿子飞了一地,又是泥又是水。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她把被雨淋湿、几乎无法辨认的书稿一张张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家用熨斗一张张熨平。
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这时候的马奎斯才三十九岁。太太和马奎斯去墨西哥城邮局,将《百年孤独》的定稿寄往布宜诺赛勒斯。邮局的人秤了包裹,算了算,说:“八十二比索。”太太数了数钱包里剩的纸币加硬币:“我们只有五十三比索。”两人拆开包裹,分成两半,先把一半寄去布宜诺赛勒斯,剩下那一半,要怎么凑钱寄过去,我们心里完全没谱。后来发现,寄走的是后半部,不是前半部。钱还没凑够,出版社的主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前半部,给了马奎斯预支稿费,马奎斯:“就这样,我们获得了新生。”
二,写作,让我们获得了新生。
也就从新生开始,但新生,往往是从悼亡的姿态展开的。而小说叙事,波赫士说,一般思考史诗跟小说的差别,在于一是诗体,一是散文体。但他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史诗描写的都是英雄人物,这也是所有人类的典型象征。而大部分小说的精髓都在于人物的毁灭,在于角色的堕落。换言之,是失败。这失败,也包括人生的各种劫难退败。病老死。
一个作家要追求“新生”,要不就必须有先知的能力,笃定走上这条路;要不,就得有疯子般的热情,逆世而行。如果我们都不是,那么,又是什么呢?
关于前者,先来谈谈最近看的两本书,一个是庞克教母、庞克摇滚桂冠诗人的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 1946-)《只是孩子JUST KIDS》,二○一○年获美国国家书卷奖。另一个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言人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所写的《ON THE ROAD旅途上》(1957),如果说海明威《朝阳依旧升起》是失落的一代的圣经,《ON THE ROAD旅途上》绝对是垮掉的一代的圣经。这是一个书写者写出了一本忠于自己的故事。
●佩蒂‧史密斯
世人认识佩蒂‧史密斯多半始于一九七五年的摇滚乐《群马The Horses》。《只是孩子JUST KIDS》是纪念佩蒂‧史密斯和亲蜜至友罗伯‧梅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 1946-1989)1989年3月9日罗伯去世时才四十二未满四十三岁,他死前要史密斯有一天一定要写下他们俩二十岁的故事。 2010年她出版《只是孩子JUST KIDS》时,已经六十三岁了。这是一本美丽不可方物的书。
二十岁的史密斯和罗伯各自逃离自己的家乡去到纽约,在那里,饱读诗书的史密斯找了一个书店的工作,他执迷于法国天才诗人韩波(Arthur Rimbaud)、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他们的十九世纪颓废派形象,滋养了罗伯,罗伯同时反过身成为最能捕捉他们形象那只利眼。罗伯后来成为巨星级的摄影家。同性恋、性虐待等惊世骇俗的题材,正是经典所在。
(生活在他方,韩波(Arthur Rimbaud):“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d’ailleurs出自这位十九世纪法国诗人名言:“在富于诗意的梦幻想像中,周围的生活是多么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总是在他方。”米兰昆德拉早期以此为名的小说,看似一部歌颂诗歌、爱情与革命的青春史诗,实则借着描写主人翁诗人雅罗米尔的一生,探讨在高压政治环境下死寂生活中的现实与梦想、生活与诗歌、行动与思想的关系。)
史密斯和罗伯原本是对情侣,后来罗伯发现了自己的“同志”性向,两人坦然面对,始终相伴。 (当时,垮掉的一代如艾论‧金斯堡(Allen Ginsberg)、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尚未老去,那真是一个当代艺坛的小王朝。)史密斯在书店打工,喜欢店里一条朴素的波斯项链,银黑两色粗线串着两片珐琅釉金属片,像一个异国风情的古老肩胛骨,十八美元,有天,一位男孩走进书店,买了这项链,史密斯只好和这条项链告别,她冲动的对男孩说:“别送给别的女生,要送就送我。”
两人四处借宿,努力存钱要住在一起,但从来没有失去要创作的初衷。史密斯21岁生日,罗伯做了一个山羊小铃鼓给史密斯,告诉她:“我们会一起创作,我们会成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想。”
并且有一天,罗伯放了一张飞鸟乐团的唱片“你是想当一个摇滚明星了”,罗伯对史密斯说:“这首歌将对你将很重要。”多年后,史密斯背上电吉他走向麦克风,唱出了第一句歌词:“你是想当一个摇滚明星了”。小小的预言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凯鲁亚克:《ON THE ROAD旅途上》
一九四七年冬天起凯鲁亚克花七年时间,四次由纽约横跨东西中部穿州走省的西行之旅程,都为了回应一个传人物酷爱探索世界放荡不羁的卡萨迪,吸毒、偷窃、酗酒、混乱的情欲……但他们始终保持对这个世界、人物的“挖”的兴趣,“挖”这个字,也是卡萨迪的思考核心。最后一次甚至远到墨西哥,生重病,几乎要了他的命。最后他花了三个星期写完《ON THE ROAD旅途上》,纪录这样的追寻,美国作家卡波堤(capote)说:这不是写作,这叫打字。里头的主要角色狄恩原型人物就是卡萨迪,叙事者索尔是凯鲁亚克自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日,《纽约时报》书评出来:在任何以追逐潮流为务,注意力碎散感受力紊乱的年代,有像一本这样的真摰的艺术品,都会是大事一件。这部小说不但写得漂亮,七是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凯鲁亚克名之为垮掉的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宣言。
三,租书店的女儿:如何讲一个重返青春的故事
我感觉到在握笔的指端,每个字的重量。──维吉尼亚‧吴尔芙
(一)《租书店的女儿》是一本追忆之书。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追忆体《哀悼日记》,巴特至爱母亲,母亲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故,他将对母亲“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歌”,以札记形式抒怀,随时随手写在了三三○张小纸片上:“(好)漫长,没有她在。”简洁情深。一九八○年二月,巴特过街被车撞送医,预言了札记诉说:“妈妈一走,我已紧贴着死亡(只等时辰到来)。”他拒绝治疗,一个月后离开没有母亲的人间。 《哀悼日记》可视为巴特为母亲立碑,也将一切作品归之母亲:“在所有我写的东西里,都有妈妈。”巴特还说“丧慯最全面的换喻(Métonymie),就是被弃。”
《租书的女儿》是另一形式的忏悔悼亡书。为一个时代,为一些人,为一段记忆,早期的《陪他一段》、《离开同方》、《旧爱》到《时光队伍》、《租书店的女儿》,所有的书写大约也指向了对某些事物的热情注视召唤,这些情感回过头来丰富了书写的意涵,由此推论,所有的作品未可说“都有妈妈”,只是这个妈妈,有时是爸爸,有时是老师,有时是丈夫。但向谁说呢?
我又想到罗兰‧巴特的句子,大雪落下,他写,“雪,巴黎大雪纷飞,很异常。想到她,一阵心酸:她再也看不到雪了。如此雪景,更何与人说。”
是的,谁解其中味?
(二)旅程展开:租书店的女儿如何写出《陪他一段》
从《租书店的女儿》开始说起
1. 1950年代军中退役下来父亲开了“日日新租书店”,店名出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新生的意涵,而我成了租书店的女儿。我的小说启蒙是严沁、依达、禹其民等言情小说及武侠小说。
2. 站在图书馆生命另一列文学书架前:张爱玲、司马中原、朱西宁、郭良蕙、孟瑶、苏雪林、张秀亚、白先勇……世界。兴生一个微小声音:“如果,我也能写小说呢?”
3. 于是,来到一九八○年。在“如果,我也能写小说呢?”之声冒出约十年,我以《红颜已老》得到《联合报》中篇小说奖,报上连载时,插画家王明嘉笔下,女主角章惜造型,怎么跟想像中严沁、玄小佛、琼瑶笔下的女主角近似极了,久违的文字记忆袭来,如此难以言喻,但内心清楚,自己是踏着哪一阶走到这一步的。我父亲说的含蓄:“以前我就是开间小租书店嘛!倒没想到影响有这么大。”我写着写着,每有评者指出我小说中情爱幻想具有通俗小说特质,是“挪用菁英文学形式探索流行小说的新可能”,我十分感谢:“哎呀!没得说的,我是租书店的女儿嘛!”
四,不算结语的结语
2007年3月26日马奎斯在哥伦比亚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与西班牙国王演讲,这年纪念《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马奎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五周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决定再版发行《百年孤独》一百万册:
写《百年孤独》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梦。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一版发行一百万册。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 ……把我这个睡不着觉的写书匠着实吓了一跳,到现在都没恍过神来。马奎斯从不讳言福克纳影响了他,而莫言,亦不讳言,深受马奎斯启发,见证文学生命生生不息。
至于佩蒂‧史密斯2010年11月17日《只是孩子》荣获美国国家书卷奖殊荣,她的领奖致词忆及当年在史克莱柏纳(Scribner’s)书店打工的日子,当时的她多么梦想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书,写一本能放在那书架上的书。她说:“拜托,不管科技再怎么进步,请不要遗弃书,在这有形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美丽。”
从“陪他一段”到“租书店的女儿” (PPT)
欢迎永远的异名者
访问:汪来昇、陈文慧
撰写:汪来昇
访问稿整理:房振坤
摄影:郑伊婷
校对:邱勇康
“我的写作一直就是陌生化的过程。我也希望一直保持这样的陌生化的写作状态,看待这个深深眷恋的人世。” —— 苏伟贞
于2013年8月16日,南大中文系为国际驻校作家,苏伟贞老师在中文图书馆的作品展,举行了开幕茶会。起初接获崔峰老师邀请撰写报导时,因毕业论文的压力迫使我有种想回绝的意思,但我却莫名地,还是接下了这份重要的“任务”。我想,与其平面地报导当日盛况,不如让这份“任务”增值,变成一份更有意义的记录。于是,我选择了以访问的形式,与苏老师有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意外的邀请
苏老师收到南大的邀请时,她正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起初,她并没预期至南大中文系驻校,加上满载的行程似乎也难以调配。然而游俊豪老师展现的诚意及空间,加上练习着与新加坡的旧日因缘,终于,她到了南大。这就是现在我们可坐在这里访问她的理由。
第三次到新加坡
以往在新加坡,是公事邀请,因此来去都有人接送,失去了近身体验新加坡生活、交通的机会;可是这次,苏老师选择到朋友家住,拉近了她与地方的距离感。苏老师不再被动地,从一个区块移动到另一个区块,而是真实地感受远、近空间感。
对她而言,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小市民生活的乐趣。就算只是在组屋区楼下的咖啡店里,喝啤酒吃小菜,都是令她羡慕不已的事。她与咖啡店服务生的交谈,也加深了她对新加坡民生和语言的认识,例如“放工”其实指下班。
课程亮点
“原来课程就是两个字:写作。我的心里就窃窃欢喜。”
原先,苏老师设计课程时,是针对一个比较多元的,以五四以降的现当代文学(中港台和东南亚),形成一条轴线来带领同学们进入文学世界。后来,她获知课程项目是“写作”,事情好像较有重心;她还调皮地说:“我心里窃窃欢喜。”
可是在她的课堂中,初步接触,她其实大量给同学们介绍一些作品及理论,希望从中能唤醒大家内心,受文学触动。她甚至有计画的在台湾编好一本三百多页的教材文本,从台湾寄来,送给学生,也方便讲授。
“你们人生还有很长的路程,这一段时间,也许会变成你们在文学上,可能甚至是唯一,最短暂却最深刻的接触。”
她希望自己离开南大后,她举例,同学们看到月亮时, “不再只是看到一个月亮”,而是能过一种看的方式,透过 “文学的心”,以较丰富的文字意象传达出来。她希望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打动同学内心的撞击者。
写作的初衷
每个人,每天都处于变化中,更何况是为作家。苏老师自第一本小说集《陪他一段》享誉了华文文坛32年,她是否能保持着那份初衷?
“其实这些年来,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一种陌生化的感觉…… 人人都活在一个日常生活里头,对习以为常的事情会变得冷漠枯燥,不会去感受。我觉得我自以前我是一个“意见者”,发誓永远要对这个世界有意见…… (不去感受的日常生活)容易使人庸俗。”
我想,“初衷”对于许多作家而言,书写时并不那么意识;但唯一确定的是,像苏老师这样的作家,她无法只是平凡。对她来说,很多事情都愿意通过“感知”去了解,而不愿意追本溯源地挖掘真相。如果说,老师的书写一直保持着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她的“感知”便是一种独特的个人“感受”。正如2005年范铭如与老师做过的访问中(《印刻文学生活志》第24期,2005年8月号),她认为“感觉”是无法与任何人“感同身受”的。
我继续追问:是否因此,您的文笔才极为细腻的去刻画人物的心灵感受?
“我并不认为我比别人感受得深刻,可是就是‘不一样’。就像同一个时间在地球上诞生的人,他们的命运不会是一样…… 我并不是说别人不了解我,就表示我比别人深刻。我写细腻是因为我本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人。我不写细腻,我没办法往下写。但比较难的是,我要怎样展现出来,我跟别人感受不一样的部分。 ”
不肯沉默的心
我在准备苏老师的访问时,翻阅了许多台湾文史与评论,几乎每一篇都指向《沉默之岛》为她的经典之作。我在网上搜索时,发现《沉默之岛》竟然是绝版书,本以为必须要到图书馆借才能阅读得这本经典。可是,机缘巧合下却在(上学期)第一届本地驻校作家,英培安老师的草根书室中寻获,像是挖到宝一样。于是,我开始很认真地阅读这本小说。
作为一本开创新时代观点/性别/情慾/跨越空间/身世议题的小说,起初读起来不容易,像是在苏老师许多形而上的思绪中游移,如果稍不认真,就会迷失在茫然的大海中,而超高密度的文字,不断地阻碍着我的前进;所以为了完成阅读,我必须顺着作者思考的巨浪 —— 这才令我找到了陆地。
苏老师认为《离开同方》是她对眷村生活的小告别,而《沉默之岛》则是向情慾书写告别,象征了一个书写的“新开始”。
“《沉默之岛》形同打开了一个视野,意思说,你好像可以飞高一点,看得清楚一点了。”
苏老师的《沉默之岛》享誉中外,(甚至即将在新加坡翻译成英语出版),被南大中文系游俊豪老师评价为“世界级的小说”。许多学者在分析这一篇小说时,就断定了作者是位“女性主义作家”,包括陈芳明的《新台湾文学史》也将苏伟贞放置于“80年代女性小说崛起”时段里。
汪来昇:不同学者给予您不同的评价与地位(眷村、女性主义等),我好奇的是您怎么定位自己?
苏伟贞:眷村小说这个部分,其实是我的一个身份。我出身眷村,眷村书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族群的创作。我很高兴自己是其中一员,我很喜欢眷村小说这个名称,我也希望自己在眷村书写这件事上出过力。我愿意在这个身份被贴标签。至于女性主义作家,会不会有点“开倒车”?伍尔芙(Virginia Woolf)作为女性小说的先驱,为女性发声,告诉世人,一个女人要自己的房间,呼吁思考。(女性主义)究竟是个限制呢还是个贬义词呢或赞美呢?
汪来昇:那您当时写《沉默之岛》时,有意图刻意把女性主义、权利的东西放进去吗?
苏伟贞:完全没有。《沉默之岛》可以说是个情慾“无性生殖”繁殖的实验,正是要去女性主义化。它同时是个雌雄同体的概念,她(晨勉)可以得到一个自身的满足。我要说的不是情慾上的满足,而是一种试探,人类的身体可以大到深化到什么程度。
汪来昇:《沉默之岛》中,有种令人穿梭时空的感觉。小说情节和晨勉思绪的广度和深度惊人;这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是否有紧密的关系呢?
苏伟贞:完全没有。但我觉得这和我长时间坐在那边(案前)有关系。我不知道别人的生活,可是我感觉和猜想,大部分人的一生也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我觉得我的生活都是我能够承受得住的。那剩下,可能只是一个对远方的向往的状态。所以在《沉默之岛》里头那么大跨度的,可能是对不安定的一种渴望。我们的生活都太密集了,包括生活的空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想要抽离,不断地在旅途上抽离。可是我是一个糟糕的旅行者,我去到哪边,我就在上面不动的。可是“另一个我”就时常代替我不断的抽离到别一个地方去。创造出来这样子的人,代替我狠狠的过另外一种生活。
如果说《陪他一段》开启了苏老师这颗敏锐的心,《沉默之岛》便是召唤她内心最深刻的自我,在沉默之中透视周遭和自省的著作,与文字零距离最亲密地接触。虽然时空无法束缚一位作家作品世界里的精彩、跳跃与开阔,但是到头来伏在案前书写的仍然只剩下自己。我想,切实面对被召唤的内心,才能在文字里展现出一种“孤独却坚持” 的张力。
曾经沧海
在整理访问问题时,我刻意标上“这题可不作答”,害怕苏老师觉得我过问她的“私事”。不过访问时,她虽然眼眶泛红,却还是和乐观勇敢地与我们倾心。我想,我不应该在这一题上“整理”苏老师说过的话,而是让一位作家真情流露地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汪来昇:您的两部作品《时光队伍》与《租书店的女儿》,得知是您失去了生命中两位最重要的男人后写下的。在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对您的写作或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苏伟贞:这样说吧,我先生跟我爸爸都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原型,我其实现在还不是那么能谈这件事情。而且,我先生可以说是我最好的一位读者,他的位置一向很抽离。我们会亲近,就是因为他看了我的小说,他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写作要求十分严格。我想我知道他的想法: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
有时候论者会把“张(爱玲)派”作为一种流派,纳入某些作家,他(丈夫)会澹澹的说:“其实你的视野已经比张爱玲宽了。”这当然是一种鼓励,以他的形式。所以他离开,然后要写他,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有这样的可能。因此,当我决定写他的时候,也看了一些人追悼文章。我希望可以告诉他(丈夫),我写得不比他们坏(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以夫之名吧。把他的一切有形无形都写到底,所以,我跟小孩说,你们不太了解自己的家谱,因为先辈是从大陆去的台湾;我还同时跟孙子讲,你们以后要是不知道张家排行辈分,就去看《时光队伍》。孙子不记得他爷爷的样子了,他(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才一岁左右。但是我说,这本书,在这里头,你会知道你爷爷是怎么样子。主要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先生的后人写的。
可是我真实世界已经找不到、可以那麽自觉的保持自己一贯人格的他了。我不知道该把他放在一个怎么样的容器里头来写。藉由我先生生病表现在状态,我觉得说,他和一些我响往的人格者真的是一支队伍裡的人,他们朝向一个我们开不见,但是仍然在行走进进的时光隧道隐去。
所以写完后,一直到现在,我陷入一种深深不太想写作了的情况裡,我居然用先生来当题材来写作。这真的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但想想,我一直想要告诉他,他走以后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又开始慢慢写了,他走以后,我们一起曾经去过的地方,现在变得什么样子了,作为一个报信者,我要告诉他。
至于我的爸爸,他的过世,其实代表我们家在台湾岛上面的一个开始与结束。我父亲1949年跟着部队从广东到了台湾,等于说连根拔起。我们在台湾除了姑妈没有其他亲人。我爸跟姑妈很亲。我这一代,是“伟”字辈,也是父亲所知道的我们广东老家谱系的最后排行。
我父亲到了台湾以后,有了第三代,于是就自己拟定了一个新族谱“立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转化自文天祥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但我父亲以“立”代“养”,这跟他出身军旅有关。我的父亲的过世,等于属于苏家在岛上的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排序延续生命,即使我父亲不在了。
当然,年纪大了,回头看父亲他们一代,以一个移民的身分被抛掷到台湾,没有任何资源,辛苦拉拔小孩长大。举目无亲,以现在的眼光看,我都会害怕,但是他们没得怕的,(只能)向前走。
我爸做过很多事情谋生,一个腰杆挺直堂堂正正的男人,他从不抱怨,自己承担。人家(父亲)以前也是个公子哥儿,在家里大爷似的,所以这样的结束一生,我认为对我父亲来说,不是一个坏的结束,他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我会一直牢牢记得回台南成功大学教书是为了我爸爸的那份初衷来做为我这一生行事的准绳。因为我知道他从来都没有料到,他有一个女儿,可以到学校当教授,而且是台南这么好的学校。那像我当初写作、得奖把他吓了一大跳同样状况。
教书这件事的可能性,在我进军校基本上已经毁了一大半,因为那不是发展学术的地方。但一切时机凑合得如此好,我唸了博士,我从原本工作的联合报离职,我进了学校教书。我开始积极回台南,是意识到我爸爸没有多少时间。也真的,我回去半年他就走了。我永远都看见,当我重新再做一个女儿,家人们围桌吃饭的时候,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坐在旁边,脸趴着桌面,一直望着我们一直微笑。他严重的重听,视力也很坏,看不见听不见,体力也差。子女们几乎都回来了,在他人生最晚的晚年陪伴着他。那个无声的画面,想着都心痛。
所以父亲过世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他走后,之前之后纪念他陆续写成了《租书店女儿》,那样的纪实有所本,对我只能以散文的形式来写。
是啊!父亲对我的影响永远大过其他作家。
给南大中文系学生的一句话
“写作永远不会太迟,因为人一直活着,就是一直在为写作这件事做好准备。”—— 苏伟贞
稿于:2013年8月25日
文章来源:华文文学创作暨驻校作家计划